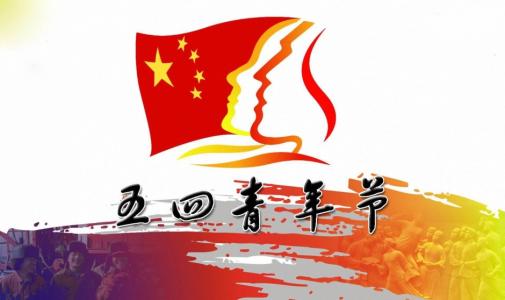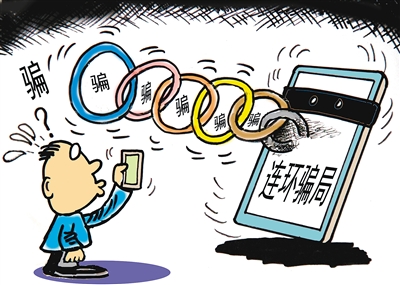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思想以及思考的能力,被很多哲学家视为“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的重要标志。无论在哪个时代,人的思考本能都无法被抑制。而青年人往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批判精神,因此也是思想最活跃的群体。
大约百年之前,正是一群意气风发的中国青年,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推动了旧社会的变革,揭开了新中国的序幕。如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很多思想也许不再适用于当今时代。但是,他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历史学家王汎森的研究,看一看一百年前的中国青年都在思考些什么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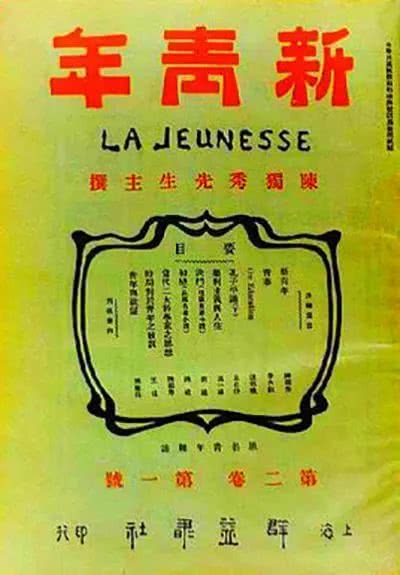
一、为日常生活而苦闷
1920、1930年代青年的文字中最常出现的是“苦闷”二字,刊物中常常出现的是“中学毕业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苦闷”这类的字眼。这反映出新文化运动后青年界常见的“烦闷”或“虚无”状态。这种“苦闷”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很明显的体现。
1924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燕日章写给萧楚女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因为家庭及婚姻的累赘,徘徊于是否脱离家庭与拒绝婚姻。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1925年3月。署名“方斌”的青年写信问《中国青年》的编者说,他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决意解除幼时家庭待定的婚约,故写信要求双亲,但始终未获许可,想要激烈处置,又怕父母断绝其经济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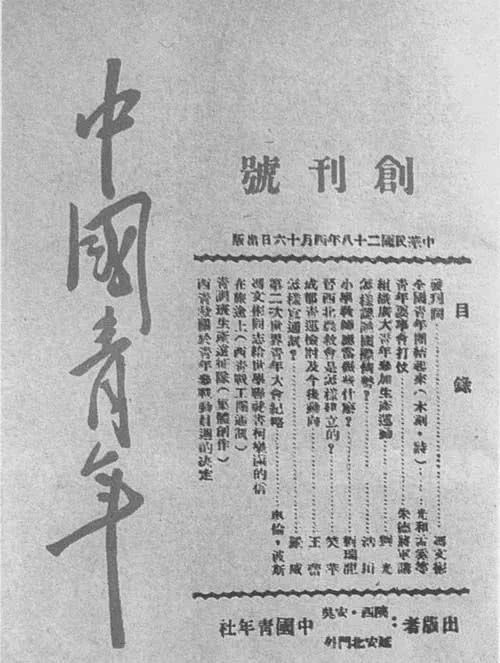
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
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担任主编。
除了家庭与婚姻之外,学业和前途也让青年们倍感苦恼。《甚么地方有较好的学校呢?》是1925年的《中国青年》中一篇文章。当时许多青年因为受了新文化运动及革命宣传的影响,不愿受教职员的“压迫蹂躏”,不愿再留在“黑暗的学校里”,于是他们困惑地问,什么地方有较好的学校呢?这是当时学生界相当普遍的困惑。
1925年,在南京的学生吴崇枢,抱怨他与多数同学因为贫困,且书价昂贵,买不起新杂志。还有一位名为张景良的青年,写了一篇《退学呢?使全家跟着吃苦呢?》的文章,同样也表达了因为贫困而影响学业的困扰。
即使解决了贫困问题,依然无法安心读书。1926年,有一位叫濮铁符的青年写信给萧楚女与恽代英说,他家做米、纸两种生意,近年来因为道路不通,外国纸、米输入日增,以致家业失败。但他受到亲友的帮助,继续在上海求学,而这些资助人是地方上的绅士,有些是土豪劣绅,本应在革命党人打倒之列,他因此感到一种道德上的两难。


萧楚女(左)和恽代英(右)
可见,当时的青年人在许多问题上都遭遇了挫折,经历着迷茫。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国初期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都处于迷茫与动乱之中,普通民众自然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地生活。
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中,主角因为受到日本艺伎的冷落,极度自卑,悲叹这都是自己国家的衰落不振所导致的。 这虽然是一个故事或一个个案,但也反映出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以及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挫折的态度。


(郁达夫及其著作《沉沦》)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策,但是我们通过下面这个关于恋爱问题的例子,也多少能够窥探出当时的青年们想法。
1925年夏天,在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担任主编的杨贤江在一个夏令营演讲青年恋爱的问题,他的言论掀起了一番讨论,于是大家提出恋爱须先从社会革命着手,一旦把旧社会完全推翻,另建新社会,“把社会上人人都变成无产阶级,大家都一律平等,到这时候,从前所谓的小姐、少爷一个也都找不出,才可以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者的恋爱问题”。
杨贤江的言论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有识之士。另外,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三民主义亦是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这一左(马克思主义)一右(三民主义)两大“主义”的崛起,为当时青年人找到了很多他们困扰的问题的答案。

(杨贤江)
二、为人生价值而迷茫
人生是个宏大的话题,即使是今天的我们也很难想清楚。在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青年亦如现在的我们,都在思考“什么是人生”的问题。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就说,五四点醒青年思考“人生”是什么,但是并未给定答案。五四确实一再说文学应表现人生且指导人生,但并未明确说明“人生”是什么。
以人生观为例,在传统中国,“人生观”是相当清楚确定的。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人们尽管未能在实质上清洗掉旧人生观,但至少在理念层次上,每每认为旧人生观有问题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人生”,面向“人生”,不是面向所谓衰腐的传统来思考什么是人的生活。过去的“人生”是落伍的,应该被打倒的。然而问题是合理的“人生”又是什么?这对新、旧或不新不旧的青年来说都是一个大问号。旧派即使坚持旧的理想,也因失去信心,不敢自持。不新不旧的青年,则不知是要旧的还是新的。至于新派,则对于新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有时也未能得到确定的答案。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因茫然、困惑而层出不穷的自杀事件,陈独秀的《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文中,他写道:“这班现代的青年,心中充满了理想,这些理想无一样不和现社会底道德,信条,制度,习惯冲突,无一样不受社会的压迫;他们的知识又足以介绍他们和思想潮流中底危险的人生观结识;若是客观上受社会的压迫,他们还可以仗着信仰鼓起勇气和社会奋斗;不幸生在思潮剧变的时代,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威权,主观上自然会受悲观怀疑思想的暗示,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上的根本疑问,转眼一看,四方八面都本来空虚,黑暗,本来没有奋斗,救济的价值,所以才自杀。象这种自杀,固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自杀;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不算是社会杀了他,算是思想杀了他呵!忠节大义的思想固然能够杀人,空观,悲观,怀疑的思想也能够杀人呵!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

(陈独秀)
钱穆在《悼孙以悌》这篇不大引人注意的文章中,也道出介于新旧之间无所适从的青年,因为对“要怎么生活”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产生困惑,最后竟至于自杀。
钱穆分析北大史学系孙以悌的自杀,其实也是在讲广泛的时代现象:“怎样生活”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他说:“当社会的秩序比较安定,政治法律风俗等等在比较有遵循的时候,做学问的人,尽可一心做他的学问,本不必定要牵涉到我们该怎样生活的问题上去”,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旧的信仰和习惯,尽量破弃,新的方面的建立还遥远无期”,因此青年们感到迷茫和失望。

(钱穆)
吴康形容一些青年是:“一生的生活,都归于‘莫名其妙’。”
柔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人’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个人,就是所谓人的一个人,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呢?”
“宇宙啊!为什么有一个‘人’的大谜呵?”
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对于人生的无所适从。这时候,就需要一种主流思想来挑起大旗,为迷茫中的青年们指引方向。

柔石,姓赵,名平福,后改为平复,笔名柔石。
中国作家、中国共产党员,左联五烈士之一。
当时儒家、佛家、道家、基督教乃至通俗宗教等各家各派都提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国民党的理论家也不例外,譬如邵元冲写了《三民主义的人生观》,强调三民主义的人生观是互助、人和的社会,其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生观。在各种人生观的竞争中,左派的理论体系更胜一筹。

(邵元冲,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为国家民族而忧虑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烦恼,还是对人生的迷茫和怀疑,追根溯源其实都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国家民族之衰落,而又不知从何处下手解救,这是当时的青年人最大的忧虑。“主义”的出现满足了人们的渴望,消解人们对国家命运模糊、低迷而又找不到下手处的痛苦。
当时救国的论调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佛教救国,基督教救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才是拯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正确道路?

(民国教育救国笔记本)
人们显然持着两个判断标准:国家是不是有办法救?社会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改变?而新“主义”提供了一张有用的救国蓝图。
布尔什维克主义或三民主义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两点不可忽视:第一,它们提供了整套的蓝图与道路,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完成社会革命。第二,是有一个以主义为指导的纪律严密的党组织,可以进行极有效率的行动。在1920年代,有不少人认为他们找打的“主义”与“党”为他们提供一条新路径,非常兴奋地觉得“报国有门”。找到“门”之后,只要开门走进去然后紧紧跟着行动就是了。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他读了马克思的书,“我总算认识了一个方向,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方向。”
黄克诚在回忆自己加入共产党之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从此,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再也没有消极过。”
在为国家民族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在为个人寻找出路;找到国家的出路时也就找到了个人的出路,两条路即是一条出路,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出路在这里合而为一。

(夏衍)

(黄克诚)
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和民族,一百年前的中国青年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很多,并且将思考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使思想成为了生活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许多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它们也都对近代中国乃至现在的中国有重大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老师的著作《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就集中探讨了近代中国的诸多思想,并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的解读。

(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