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6月16日深夜,靠近北极圈且人口只有32万人的冰岛,首进世界杯以1:1战平两届冠军阿根廷。如同“午夜日光”,天光乍现,全世界人们为“冰火之国”烈火赤焰般的登场而惊艳赞叹!这一天已临近夏至。
夏至一般自6月21日前后开始,“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至者,极也。”夏至来临之日,太阳直射点在北回归线上,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时间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且越往北白昼时间越长。冰岛在北半球极北之地,冬季长夜蛰伏,夏至前后,日照时间可达21个小时,凌晨3点不到就天光即明,午夜12点太阳依旧迟迟不落。热爱足球的冰岛人们却乐得在夜短无梦的时光里逐日争时、挥汗如雨,成就了2018年世界杯“午夜日光”般的梦幻传奇。

在我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进入夏至后,逐渐昼长夜短,人们在惜时如金中,也开始迎来35度以上高温暑热屡见不鲜的日子。记得小时候,每到这时,太阳光便早早落在了床上,透过眼睑把梦都照醒了,由不得你睡懒觉。一爬起来,后门的台阶上早已是一派忙碌拥挤的景象,母亲已经用搓衣板把全家的衣服洗了头遍,父亲也早已准备好水桶,挑着担子从后门去“大井眼”挑井水,顺带拎着衣服去旁边的“细井眼”漂洗。

“大井眼”,水源不绝,绵延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资江河畔的家乡,夏至前就有“端午涨大水”一说,若是持续降水,河水极易泛滥,难以取用。于是人们四处查勘,在入城不多远处发现了地下暗河,就地掘井,成为小镇主要的生活水源。我家后门的弄子是河边老街前往“大井眼”的必经之路,进入夏至,挑水洗衣的人愈发多起来,担子里的水晃荡得多了,整条弄子都水潞潞地泛着光,地上的青石板被井水养得沁凉,房子的青砖基脚沾了潮气,泛出一层层葱绿的青苔,从后门一下台阶,穿堂风凉爽爽地迎面吹过来,只觉得顿时清凉。

到了暑假,母亲索性让我们搬了条凳和矮凳,在弄子里做作业。上午的时候,弄子里倒也安静,偶尔从弄子深处走来三两个人,都是挑着担子卖瓜果的人前来歇脚乘凉。夏至,正是桃红、李黄、瓜甜的时候,卖瓜果的人进了城多半先跑到“大井眼”把瓜果泡得冰冰凉凉脆生生的。一眼瞟过去,西瓜跟碧玉一样溜滑、透着阳绿的光;李子熟得仿佛可以看见玛瑙般的肉汁把皮都快撑开了;桃子最美,桃子尖尖上的红像是醉美人腮上的一坨酒红,浓得化不开,桃子蒂上依旧青绿带春,琥珀样的桃胶粘在桃蒂上,凝脂一样的挂着水珠。卖瓜果的倒也大方,看我们眼睛瞅着不放,掏出几个碰烂了的瓜或果给我们,我们也推辞不要。心里其实亮堂得很,呆会儿他们一穿过弄子,就到了街面上,外公对哪个时辰卖瓜的会来,哪家的瓜好,他老人家心里有本帐,早就坐在门口的荫凉里“守株待兔”了。到了晚上乘凉的时候,他老人家把上好的西瓜、桃李从水缸里一把捞出来,我们在凉席上只管排排坐好,人人都有口福。

午后,弄子里乘凉的人渐渐多起来,我们也已经把一天的作业做完,几个兄弟姐妹一撺掇,集体往“大井眼”边上的“转坑”跑。“转坑”是连着“大井眼”、“细井眼”的一条溪,也就三四米深,溪边长满了不知名的花草,我们也不知它转了几个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再热的天气,有了水,就有了清凉。我们最高兴的是坐在热得“烫屁股”的青石板桥上,伸出“脚丫子”,把水花踢得老高,或者是沿着窄窄的岸边,捡来瓦片片打水漂,又或是将水枪汲满了水,把别人打得一身透湿。

玩够了水,太阳越来越烈,知了闲坐枝头,鼓翼而鸣。我们懒得听它呱噪,夏至时节,越来越多的蜻蜓才是我们追逐的对象。那些金黄的、孔雀蓝的、赭红的、青黑的翅膀在阳光下颤动着,像鎏金的薄得透明的绸缎流光溢彩。我们也顾不得太阳晒得肉疼,屏住呼吸,一次次地扑空,一次次地想捉它来看个真切。“转坑”边的萤火虫倒是又笨又呆,它们往往藏在菜地里的南瓜花、丝瓜花上,滚得一身黄色的花粉,我们一捉一个准,一会儿功夫就把带来的药瓶子装了一小半,在瓶子上拿针钻几个孔,放在窗台上,等到晚上全家人纳凉的时候看它们在夜光里一闪一闪。

到了下午三四点,街面上的叫卖声也夹杂着燥热不安,突然的喧闹往往是挑担卖菜的人中了暑。记得有几次,街坊扶了中暑的人上门来找外公求助。他老人家倒也不慌不忙,把人扶进不透风的里屋躺下。外婆不知什么时候已从厨房里倒来两碗温开水,一碗递给外公,一碗在水里丢下三个大小不一的银元。只见外公就着碗里的水洗了手,用手指和中指在病人的眉心上用力地扯起来。外公一双手削瘦而纤长,平日里只见他读书写字,斯文得很,这会儿见他的手倒有点像老鹰的爪子,弯钩之间有着精瘦见骨的劲道,中暑的人鼻梁上顷刻间便浮起了紫色的一道竖杠。紧接着,外公把人扶起来坐好,把他身上的衣服翻过来往上一卷,侧身含了一口水,“噗”地一声顿时水花四溅,匀匀净净落在病人的背上,他老人家用食指和中指夹起银元飞速地在病人背上刨刮,并不看见银元落在背上,就像立在“转坑”边那苇草上的蜻蜓,突然间振翅而下,却从水面上一掠而过。眼看着一条条“痧”痕经天纬地般在背上冒出来,由浅红至黑紫,外公这才放下大的银元,再用小银元在头颈处、手腕处细刮一遍,不急不徐,直到外婆再次端来温热的盐开水让中暑的人喝下,面色如常。

外公年轻时候就走南闯北做生意,也不晓得跟谁学的这门子手艺。我们兄弟姐妹,夏天里贪玩贪凉贪吃,免不了寒暑不调,头疼脑热,人一打蔫都跑来找外公。他从不给我们刮痧,只拨筋。我们搬根小板凳,软耷耷地靠在他膝盖上,他把我们的手一把拽过来,大拇指在手腕、手肘、腋窝一压一探,再快速一拨,用他的说法,“只听到崩崩地响”,我们全身就跟通了电流似的,从头到脚,由上至下,痛痛快快麻了个爽透轻松!他不在家,我母亲和外婆也学他的样,可就算掐得我们身上起了印子也没摸到“麻筋”,只痛得我们喊,咯得我们笑,一边扭着身子一边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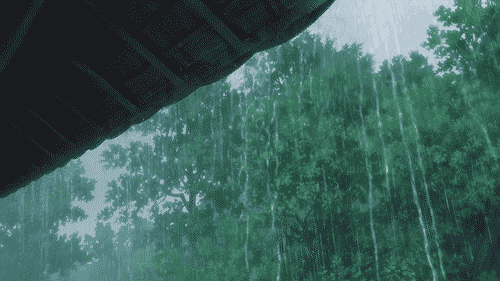
暑热难不倒我们,困住我们的是雨。夏至的雨下起来黑天黑地,瓦檐上的水如同千根万根的银线,流个不停,我们哪儿也去不成。有时候,风一大,就直往堂屋里扑,外婆索性连门都关上,屋里黑魆魆的,苦闷得很。间或,门前下水道的“瓮眼”里,雨水“汩汩”地由里往外冒,再漫过台阶、门槛直往屋里渗,外婆便一手打伞、一手拿着长火钳,一边捅“瓮眼”一边往“转坑”望,回来对外公说,只怕要涨大水了,“转坑”里的水快要澎出“衔”(方言,通“沿”)了。外公说,怕什么,大不了搬到石山岭去!石山岭在城郊,是县城最高的地方,我心里遥遥地想,爬个山就到了,我正好还冒上去玩过呢!

真的大水来的时候,是1998年的夏至,持续的降水让资江河里的水一次次澎了“衔”,到最后“转坑”里的水不断往老街倒灌回流,外公住的房子很快淹了一米多高。外公是老街最后一个撤离的人,他在二楼气定神仙地说:“慌啥,夏至,夏至,天有极致、人有办法。1931年、1954年都是这时节发的大水,不也过去了吗”?最后,还是父亲和小舅把他霸蛮背出来,在越涨越快的洪水中用澡盆把他推了出来。洪水消退后,天气持续暴热,外公再也没有力气帮别人刮痧祛暑,他听着屋外的蝉鸣,在自己的家里安然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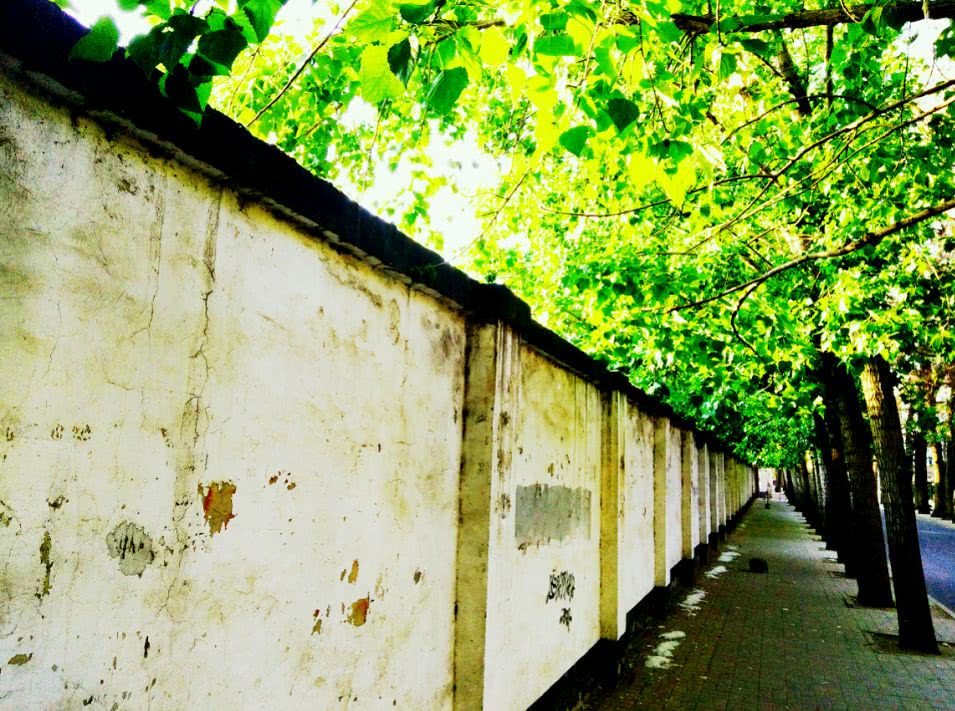
那一年的“大井眼”、“细井眼”、老宅、弄子,还有我们心心念念的“转坑”全部埋在淤泥中,等待整修。再回到家,我站在修葺一新的街口找不到屋门,怅然若失。
夏至,夏至,天有极致、人有办法。冰岛热爱足球的人们在天象奇观里,秉承刚健、自强不息,踢出“午夜日光”的璀璨传奇;家乡的孩子们赤子初心、至性而为,把暑热玩成了童趣清欢;老人们在暑热难耐与滔天洪水中“顺天时、适寒暑”,始终保持了知天乐命的清醒。夏至,至者为极,却造就了属于大千世界的传奇与精彩!(本文图片来源于摄图网和视觉中国)
(来源:腾讯新闻)







